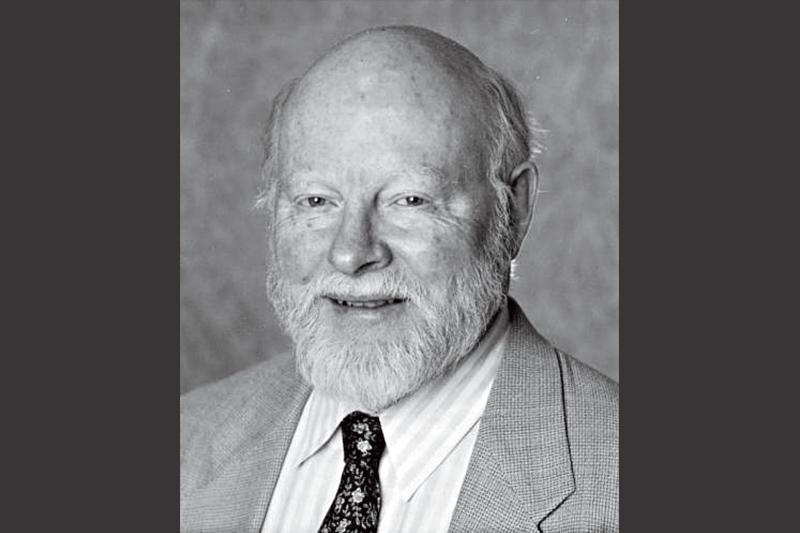文丨陆磊
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
在当前或许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,我们对经济波动的原因及其管理的认知仍然是表层而粗浅的。究其因仍然是理论的薄弱或误入歧途。比如,在短期,需求管理与菲利普斯曲线构成了主流认知体系——即在总供给滞后调整的前提下,总需求和需求结构决定了增长、就业和稳定。因此在政策响应上,逆周期需求管理是惟一手段。但是,这势必引起中期供给变化:如果我们通过外生的财政或货币手段人为增加需求,则在中期,供给曲线势必因需求增减而在生产函数(技术)既定的前提下相应平移,但受到要素投入量的制约。
或许这说得过于理论化,那么,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就再浅显不过了:比如当通过购置税补贴(财政政策)或优惠利率分期付款(消费信贷政策)鼓励汽车消费,则在即期会形成对汽车厂商的新增订单信号,并进而构成其扩充生产能力的激励,因而在中期形成供给增加;而长期影响是,不断诉诸短期政策外生调节,势必导致微观经济部门景气总是与资源投入量有关,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要素“质”的提升(包括人力资本、资源和环境)、转方式和调结构就无从谈起。这一影响进入超长期,我们会惊讶地发现,整个经济体陷入了对政策当局短期调节的过度依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