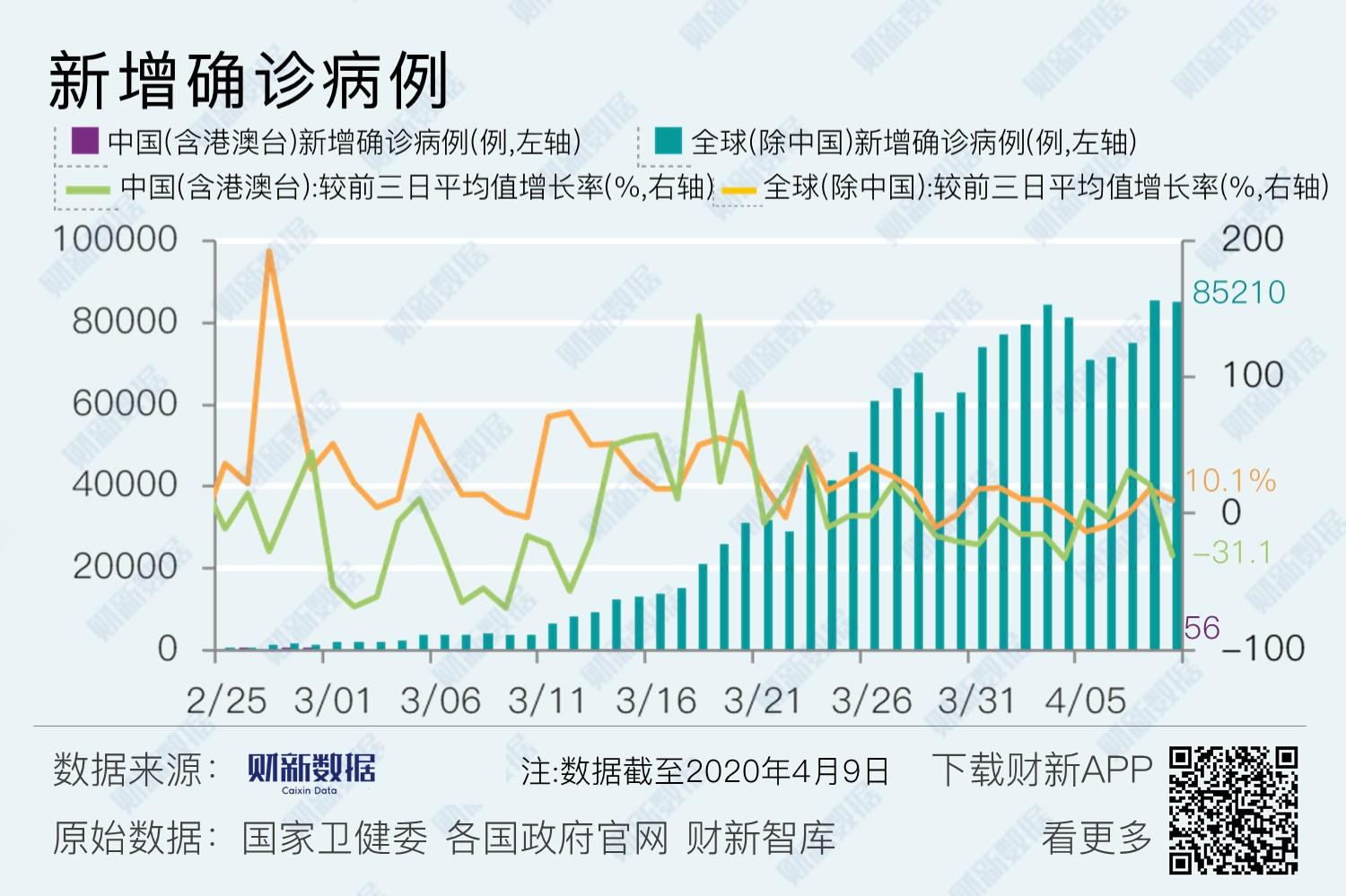文|张宗子
作家
自3月中旬开始,纽约疫情逐渐严重,15号周日晚上,市长终于下令,中小学全部停课。星期一,我工作的图书馆宣布闭馆。那天早晨,在赶赴位于牙买加区的办公室的路上,我第一次戴上了口罩。图书馆小餐厅已经停业,去附近的甜甜圈店买咖啡时,收款的印度女士问我,是中国人吧。我说是的。她似乎富有深意地笑了笑,没再说话。那时候,华人之外的美国人,对于疫情,都觉得无限遥远,与己无关,就像埃博拉发生在非洲一样。简短的部门小会之后,同事们大包小包收拾东西,像搬家,又像撤退。我没有什么可收拾的,只把借出好几天的一本西方哲学史普及读物带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