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|杨葵
作家、策展人
听流行歌曲,喜欢单曲循环。意不在听,只求有个响动做背景声,手头零七八碎,该干嘛干嘛。有时,歌里一两个词,又或是一两节音符,会带跑心绪,到爪哇国云游半晌,再回人间世。
今天听卢冠廷《一生所爱》,一遍唱完,沉默片刻,第二遍再起,如此往复。每次乐声重现,冲进耳朵的前几个字都是“从前现在”,某一瞬突然就听进去了,思绪随之游走。
人过半百,有很多“从前现在”可说了。
还是听歌,前些天听黄霑唱他写的名作《沧海一声笑》(一直觉得这歌名写错一个字,“笑”改“啸”似更贴切)。词作者,非专业歌者,唱得像说话,倒亲切了,歌词从头到尾,听个一字不落。边听边想,从前听这歌真痛快啊,蠢蠢欲动,想中流击水,想浪遏飞舟。后来听这歌,听出老油条的味道,还听出虚张声势的豪情。现在听,既没有什么痛快,更没有什么虚张声势,不过是婉约到甚至有点粉气的一襟晚照,很柔情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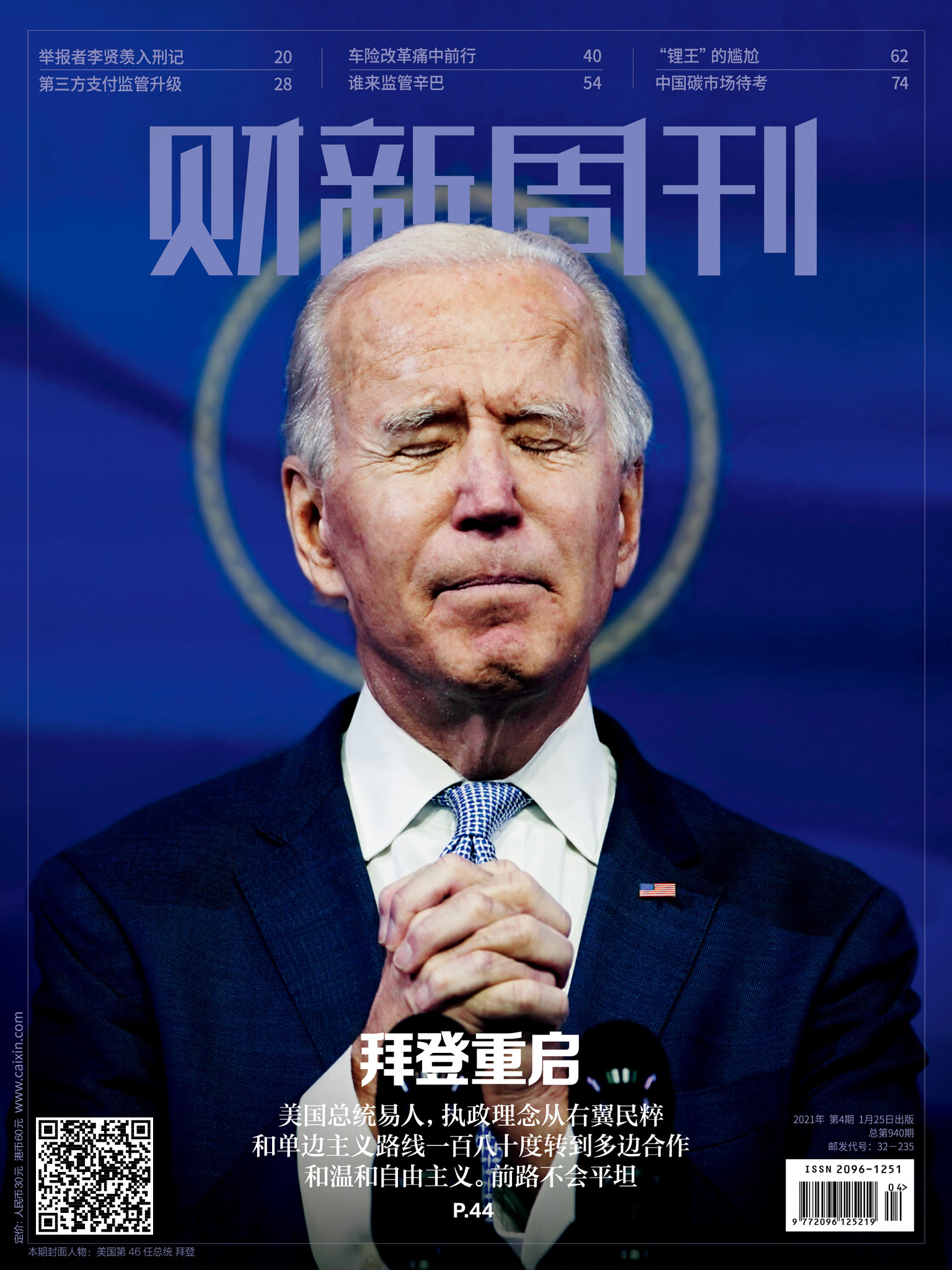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