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|南翔
诗人
某回在福建,我把一位老先生捎到几公里外的镇子。到了不通其方言的地方,我比平时还沉默一些,这是吃了教训的;以前我常向本地人打听道路,结果总不如意,——对方越想说清楚,我越糊涂,对方越是热情,我越是急于离开,因为我仅有的一点判断力,正在这种复杂的交谈中丝丝消逝。我说了谢谢,佯装了笑容,离开时比起初更加迷路,先前只是拿不准,此时可是完全找不着北了。
不过这位老先生是能说一些官话的,所以我们一路上聊天,倒也不是各说各话。老人家告诉我,他到镇上是打⋯⋯“打什么?”我忘了教训,不幸地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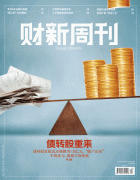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